从摩托罗拉到复旦
刘冉最初的想法很简单。他看到中国的高校和科研院所在体制上、方向上正在变革,希望能够将国外的理念结合进来,为母校在微电子领域与国内外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合作交流方面多做些实事,然而做起来并不容易。
本文引用地址:https://www.eepw.com.cn/article/92520.htm刘冉回到复旦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组织“985工程”复旦大学微纳电子科技创新平台的申报和筹建,当时申请到一笔可观的经费,对复旦大学在微纳电子技术研发能力的提升起了很大的作用。然而,刘冉感到中国近些年来在科研上的投入很大,在某些领域甚至不亚于发达国家,但是收效却不明显。庞大的投入多数用在外在的“硬件”建设上,而在内涵的充实和“软件”的建设上往往跟不上,这极大地制约了中国建设世界超一流研究型大学的脚步。在这方面创办历史不到20年的香港科技大学却能后来居上,跃居世界一流大学的行列。同是中国人,他们何以进步如此之快?答案很明显,香港科技大学在吸引人才方面舍得投入,用重金网罗到最好的人才,加上健康的运作机制,使得学校的科研和教学水平得到快速的提升。
而中国的科研院所在体制上还存在一些弊病。首先是效率低,教授每天忙于“太极拳”式的事务性会议,“疲于奔命”于科研项目申请、评估和验收;其次是庞大的关系网和盛行的“潜规则”,往往使海外回来的人很难适应。“将几个海归放在中国固有的体制框框中,他们如果想按照国外的方式去思考、去工作,势必会和周围环境发生碰撞,很难有效地发挥作用,更不可能改变周围的环境,尤其是带领一个早已成型的团队,“同化”几乎是唯一出路。”尽管如此,刘冉对于自己的选择并不后悔,他认为要想有所变革,总要有人来“踏雷”,即使“牺牲”,也会留下一些经验教训,对后人会有所帮助。
在复旦的四年多里,刘冉促成了复旦与瑞典皇家工学院,英国卢瑟福实验室,德国Chemitz技术大学、柏林工大、Fraunhofer研究所等在微纳电子领域的多项国际间合作,加强了与Novellus公司在铜互连方面的合作,以及与中芯国际等国内公司的合作。
对于中国的产、学、研脱节问题,刘冉有着自己独到的看法。“中国的微电子企业相对年轻,技术水平相对落后,很多工艺技术还依赖引进,而工艺技术的消化吸收并不是高校的强项。”刘冉认为,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工艺发展需要很多的积累,各环节需要控制得很好,不是攻克了某一道工艺就可以了,它需要坚实的基础。“国家“十一五”规划中大力发展集成电路技术将会极大地推动本国微电子行业的进步,但发展要有一个较长的过程,要靠知识、经验、设备、技术等方方面面的积累,而这些我们还很欠缺。”刘冉强调,“中国的高校以及科研院所的研究方向则应该多“向前看”,尽早布局一些前瞻性的研究,一旦技术成熟即可推到工业界。”刘冉认为,向“MoreThanMoore”和超前性的“MoreMoore”技术方向发展也许可以找到中国半导体产业同先进国家同步的突破点,国家应在这些前瞻性、探索性领域多投入。
“高校、科研院所和企业的研发中心间的联系应更加紧密,”刘冉认为,企业研发部门的研究人员可以在高校作兼职教授,而高校里的教授也可以在科研院所及企业的研发中心兼职搞开发,这样做,信息、资源、人才可以共享,“今后高校、科研院所及企业的研发部门必须要密切合作,否则单打独斗很难成气候,如果高校与科研院所及研发中心的合作都做不好,就更谈不上与产业界的合作了。”刘冉认为此次“国家重大专项”将是一个很好的契机,希望借此能够推动产、学、研间的衔接。
回国一晃已经四年多,这期间也有一些国外公司来挖角,如果单从经济上考虑,刘冉可能早已回到工业界,甚至已回到美国,但刘冉对自己的选择丝毫没有后悔。尽管国内的现状还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中国这几年的变化与发展始终鼓舞着他,他舍不得他的学生,舍不得他的母校,更舍不得他倾注了多年心血的复旦大学微电子研究院和他亲手带大的微纳电子科技创新平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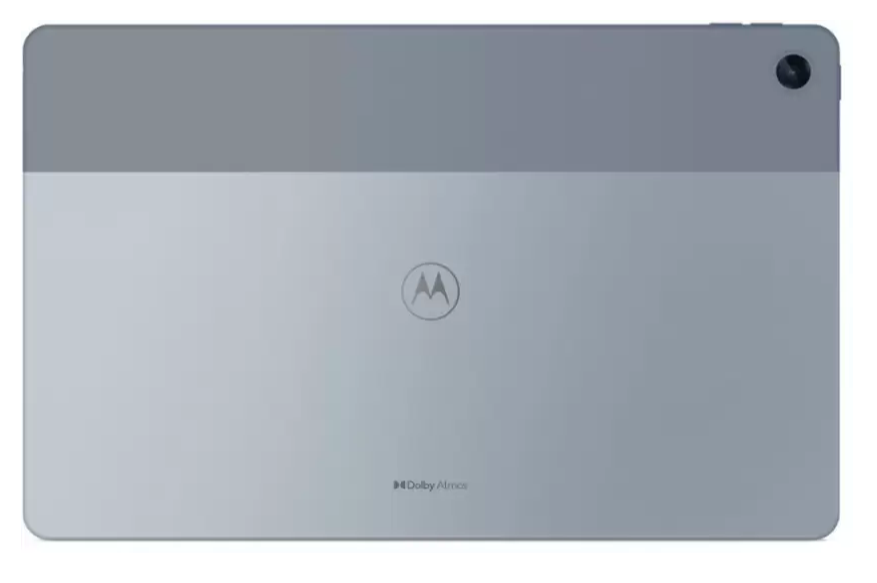






评论